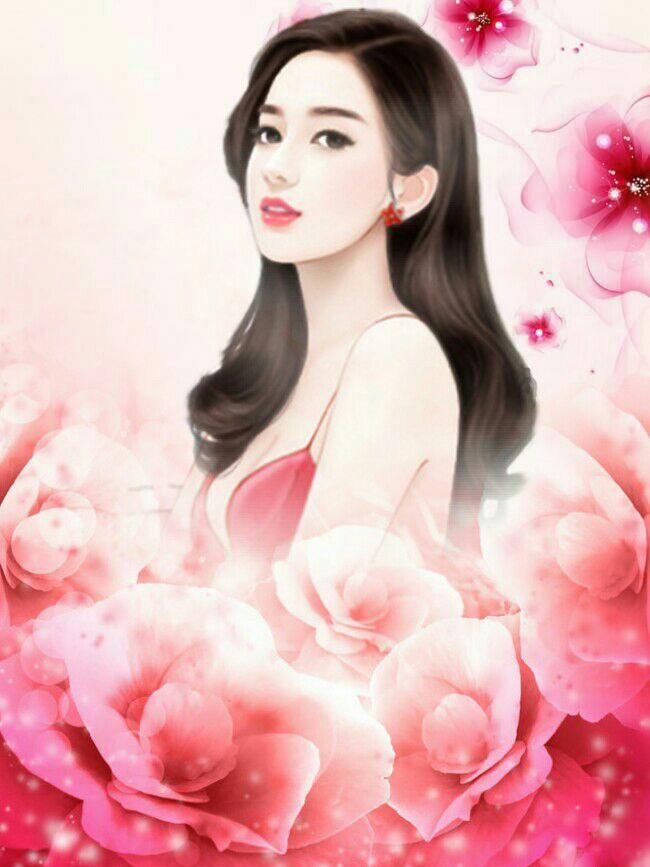全本小说>作古的意思是什么 > 第52章(第1页)
第52章(第1页)
准确来说,这只是一道裂缝,基本难以容下一个人。好在他如今还没长开,倒也能正好容下。
郁危蜷着腿缩在里面,感受到那种冷意终于驱散了些。他低着头,看见衣领口已经睡着的小山雀,后知后觉地犯起困来。这一次他没来得及再用同样的方法撕扯脚腕的伤口来换取短暂的清醒,眼皮便支撑不住率先耷拉下来,瞬间没了意识。
梦里混混沌沌,他一会儿看见几张陌生讨厌的脸,指着他骂着一些不堪入耳的话,一会儿又看见那只腿断了的小山雀,哆嗦着停在悬崖边摇摇欲坠的树梢上,而它的几个伙伴就在一旁的枝头,无动于衷地看着。
到最后,画面中的影都散了,落雪声和风声都听不见了,他回到了昆仑山脚下,被人粗暴地拉扯着,踉踉跄跄地往山上走,走得不明所以,也对接下来的事情漠不关心。
那个人边拽他边说话,声音让他觉得无比嫌恶:“……你待会老实点,再敢咬人,我一定打断你的腿!”
闻言,他看向那个人的手,上面有一道狰狞的伤疤,像是被人活生生撕下了块肉。他看着,莫名觉得很快意,笑出了声。
那人立刻扬起了手,一个巴掌就要毫不留情地落下来。他冷眼看着,没动也没反应,那人却似乎想到了什么,有些后怕,中途硬生生停住了,嘀咕道:“这次饶了你……”
不过下一瞬,那只手恶狠狠地掐住他的脸,一字一句地威胁道:“你听好了!上了山给我老实点,不然你就等着毒发吧,敢坏了我的事,剩下的解药你一点也别想拿到!”
听见“毒发”两字,他指尖颤了下,紧接着手臂传来一阵大力,他险些摔倒,被扯着继续赶路。
就这样不知走了多久,那个人突然停了下来,换上了一副笑脸,松开他迎了上去:“仙君,仙君请留步!小的是云方的修士,姓楼,单名一个涣字……”
他兴致缺缺地听着对方自报家门,面无表情地抬头看了一眼。
被拦下的那个人似乎是正要下山,路上突然杀出来两个陌生人,他好像也有点意外,却没有多么关注,看上去就像礼节性地停了下来,随意地听了一下。
楼涣站在那人身边,立刻便形如褪色无物,成了不怎么起眼的尘埃。他停下踢石子的小动作,视线扫过那人皎洁如月色般的银白长发,呼吸微微一滞,随即目光下意识地下移,对上了那人的眼睛。
那人也在看他,目光很淡,不知为何,那一丝随和的气息忽然散了。
楼涣急忙继续道:“听闻仙君近来曾带了一个少年进昆仑山,那可是几百年来的头一位,可是仙君最近有了收徒的意向?这小子灵台根基极好,天赋异禀,是难得的好苗子。您孤身一人,不如收他做徒弟,正好也解一解闷……楼九,过来!”
听见声音,他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是微微蹙起眉,不显情绪地盯着眼前的陌生人。
楼涣沉下脸:“楼九!”
没等继续说下去,他忽然收敛了脸上的神色,垂下眼,听话地走上前来,一言不发站好了,竟出乎意料地显得温顺。
那人的目光很轻,扑扑簌簌,像一片洁羽,扫在他的脸颊。他莫名地感觉到一阵紧张。
过了许久,他听见一道低沉悦耳的笑,疏远有度,不急不缓。这声音悬在头顶,随后平淡沉静地落下来,震得耳膜微微发颤。
“没有那回事。”
是漫不经心的回绝。那人微微笑着,语气也礼貌到一种生疏的地步:“——我不缺徒弟,也不需要人解闷。”
……
郁危眼睫动了动,缓慢睁开。
小山雀已经醒了,在怀里拱来拱去。吸进肺里的空气冰冷刺骨,他轻轻咳嗽了一声,头沉重得抬不起来。
脚腕已经麻木了,感受不到疼痛,不知道算不算一件好事。郁危抱着一小团暖暖的小山雀,很轻微地吸了吸鼻子。
天还亮,距离明如晦回山还有还几个时辰。等他这位师尊回来,就可以在山崖下收获一枚被冻成冰雕的便宜徒弟。
早知道会冻死在这里,他还不如继续做那个“楼九”,顶多不过是挨骂被打,才不要一时鬼迷心窍,跟着一个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跑到山上来。
凛冽的寒风卷着残雪刮过山壁,发出呜呜的呼啸声,路过他栖身的狭隘洞口时,骤然被撕扯得无比尖利,一瞬间拔高了几个调,仿佛一只无形的手,硬生生要将他们从洞中拖拽出去。小山雀啾啾地叫起来,郁危抱紧它,往缝里面又缩了缩。
在这短暂的对抗中,他忽然听见一阵轻微的踏雪咯吱声,很快又淹没在风中,虚幻得不像是真实的。
仿佛是幻听——明如晦从来不会这么早回来的。
脚腕的伤势处涌进无穷无尽的寒意,深入骨髓,从心口和肺脉却烧起一团火来,沿着四肢百骸,仿佛要将血液烧干。昏昏沉沉中,似乎有一只手贴上额头,手心裹携着新雪的沁凉,激得他微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
然后那只手又抽离了出去,他的心也被抽空了一秒,不过没过多久,他的额头就又被裹住。这次手心温热,郁危勉力睁开眼,摇晃的视野中人影也是模糊的,他怎么用力也看不清。
“别动。”熟悉的声音响起来。
郁危小幅度地挣扎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他脸颊烧得泛红,嗓子疼说不出话,只能睁大眼瞪着对方。
高烧带来的头晕和不适让他眼眶发红带着湿意,明如晦用指腹在他眼角抹了一下,低声问:“怎么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