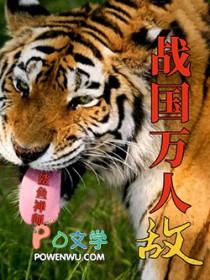全本小说>给神仙郎君冲喜全文免费阅读 > 第2章(第1页)
第2章(第1页)
&esp;&esp;医馆虽然能治病救人,却绝非是什么好去处,尤其是县里的大医馆。
&esp;&esp;除了医药费用,每日还需支付粟米两升,柴炭钱三百,重伤重病的,没个几十两银子都下不来,足够把一家子拖垮。
&esp;&esp;“可怜哎。”魏婶子道。
&esp;&esp;钱婆婆瞧着那逐渐远去的鲜红背影,最终也只能叹息了声。
&esp;&esp;芜河村东尽头,临近芜水河畔,是座已经有些年头的破旧宅院。
&esp;&esp;矮墙上的白灰大多都已经剥落了,露出里面青黑的泥砖。
&esp;&esp;阮祺压住被风卷起的衣角,站在门前深吸了口气,心底默念着等下成亲要做的事。
&esp;&esp;拜堂,祭神,合卺,同榻。
&esp;&esp;按照规矩,冲喜不能有外人在场,先前与他做交易的仆役已经提早离开。
&esp;&esp;接下来的一切都要阮祺自己来完成。
&esp;&esp;旧宅的大门没有上锁,伸手稍稍用力便能够推开。
&esp;&esp;前院杂草丛生,四周到处都透着潮气,黏腻又沉重,身处其中,仿佛浸泡在深冬的冰水里,直叫人遍体生寒。
&esp;&esp;“哗啦”。
&esp;&esp;远处传来细细流水的响动。
&esp;&esp;阮祺打了个哆嗦,不敢在原地停留,越过地上的杂草,快步朝屋内走去。
&esp;&esp;好在房间里还算整洁,外间灶台铺了洒金的红纸,上头摆着神龛和果盘,两边立着雕喜鹊祥云的大红喜烛。
&esp;&esp;都是村里成亲时惯常用的布置。
&esp;&esp;看见熟悉的事物,阮祺稍稍安下心来,点香祭了神像,又自己和自己拜过天地,确认没什么疏漏后,才试探着开口。
&esp;&esp;“那个咳,夫君?”
&esp;&esp;这一声自然不会有任何人回应,但阮祺还是开口道。
&esp;&esp;“已经拜过天地了,接下来该喝合卺酒了,你现在起不来,我喂你稍稍喝一点吧。”
&esp;&esp;怯生生的嗓音回荡在周遭,阮祺紧攥着自己的衣角,鼓足勇气迈进里间的卧房。
&esp;&esp;卧房并没有太多家具摆设,只有靠墙角处摆放着一张架子床。
&esp;&esp;帷帐掀起,露出里面清晰的人影。
&esp;&esp;那是才刚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子。
&esp;&esp;双眼紧闭,大大小小的伤疤几乎遍布全身,脸颊和前胸处尤其严重,大片焦黑的痕迹已然分不出原本的肤色。
&esp;&esp;简直像是整个撕碎后,又重新拼凑在一起的。
&esp;&esp;阮祺瞧了眼便再不敢细看,慌忙撇开视线,望向床头上摆放的酒水。
&esp;&esp;酒具是仆役事先预备好的,没有酒瓢,只有一壶竹叶青,及两盏普普通通的白瓷小杯。
&esp;&esp;“来喝合卺酒吧。”阮祺开口道,努力稳住发颤的嗓音。
&esp;&esp;不能出错。
&esp;&esp;村中的族老教过他,冲喜每一步都有固定的章程,若是哪里出了岔子,很容易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