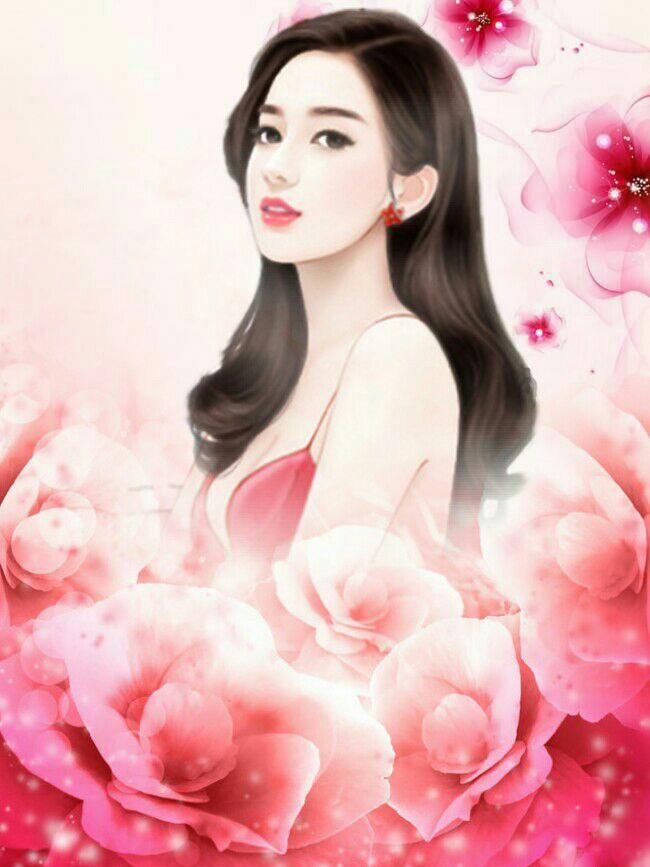全本小说>盲日什么意思 > 第61章(第1页)
第61章(第1页)
但是不管怎样,市局逐渐恢复了早七晚六的生活节奏,上上下下对她的评价还算不错。因此在她的推动下,汤麦的回归是计划中的,意外的是这回是汤麦主动递交了入队申请,经过三个月得审核、复查,合格后的第二天就来报道了。
任绘猜他一定早就装不下去了,什么医者仁心、慈悲为怀,哪里适合他们的辣手摧花、铁血无情的汤大法医呢。
如今他们能够再相聚也说明案件解决得十分漂亮,曾力、黄贺死有余辜,悉数财产全部被没收,胡梅和黄芮衡也因罪入狱,等待审判。而盲刀案因诸多疑点还未解决被提交最高机关做进一步分析,案件随之等级上升,不再是柏州市公安局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情了。
好消息是,谭享、任绘、李维仁、汤麦,在破案过程中有优秀表现,破例被省公安厅列为联合办案的名单之内,可以和一线人员共享案件进展过程,等候破冰之际再度启航。
只是,还有一个人还没去报道。
那晚之后宇唐没有归队也没有联系任何人,配枪被挂失处理,市局权衡之下对他的处罚是去社区派出所锻炼两年,还是考虑到当时情况,惩罚不算重也不算轻,主要还是要做个表态,让他能够记住这次教训。
他们一直觉得宇唐是个能屈能伸的孩子,应该不会因为这点事儿和整个刑侦队闹别扭。可是问来问去,只有最后和他通过话的谭享知道他想休息一阵子,同时他又觉得那番话是宇唐的气话,不能相信,但刨根问底之下他也说不上来宇唐躲在了哪里。
总之就是每一个让人省心的。
下班前,最后一个箱子也紧跟着被送到了法医办公室门前,汤麦正在挑拣物品,分门别类地重新摆放整齐。
他有许多书,大多都是工具类的,或是一些期刊杂志,光是看着封面就会让人忍不住叹气。但是在那堆医学辞海中,谭享偶然间发现几本花里胡哨的漫画书,问道:“汤老师,不解释一下?”
“哦,有人暂时放在我这里的。”
“谁啊?”
“……谭享,你无不无聊?”
“无聊才问的嘛。这又是什么……”
汤麦瞥了一眼他手里的铁皮盒子,说道:“这些东西都是同一个人寄给我的。”
谭享警觉,“盲刀案?”
“应该不是。就是一些……一些没什么意义的小玩意儿。”
汤麦拎起袋子哗啦啦倒出来不少东西,有陀螺、拨浪鼓、棒棒糖、半盒饼干、铁皮徽章、冰箱贴,等等等,如他所说的,意义不明,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寄出的,倒是每天晚上八点十分准时地出现在他家门口。
谭享若有所思,“最近有什么异常吗?比如有没有什么人跟踪你?地址泄露太危险了,还是要和市局打个招呼的,以防万一。”
“不用了,反正最近我不怎么回家,要在这里加班。”
汤麦算是正式安定下来了,之后他还要补上尸检报告、结案报告、这个报告和那个报告,再加上停用太久的法医室实在有些陈旧,不趁手的工具扔的扔,换的换,得忙一段时间了。
焦头烂额的一个下午,他偶尔会想到宇唐的事情,但很快又被新的头绪占满,如此状态循环往复,直到所有物品处置得当后,一种更加空虚冷寂的感觉才真正侵袭全身。
越是想要淡化,他留下的痕迹就越是明显。
在此之前,汤麦从没有过如此强烈的、对某个特定的人的思念。
门外感应灯亮起,脚步声匆忙而至,来人探头探脑地往里面看了一眼,不知道汤麦失望的表情是为何,怯生生地问道:“那个,汤老师,是任队长让我来找你的,有个案子想请您看一眼……”
汤麦叹了口气,接过报告翻阅起来,“简单介绍一下情况。”
“死者男,三十岁左右,于今日清晨在郊外水库的岸边被发现,勘察后发现肺部有大量积液,现场没有脚印,但是我们在附近的芦苇荡发现了被折断的芦苇,初步怀疑是被人劫持至此后溺水而亡。还有就是……”
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汤麦点了点某张模糊不清的现场照片,“任绘让你直接来找我一定有她的道理。不止这一张照片,对吧?”
“没错。”那人从牛皮纸袋里又拿出厚厚一沓子,“任队说了,这些照片务必交到您这里,还说……还说这是她专门从省厅档案库里调出来的。”
汤麦笑了笑,“明白,我就在这里看完。这些照片都是什么来历?……”
惨不忍睹的现场,熟悉的分尸方式,全都是案发于两个星期前,汤麦感觉自己手心发烫,越看越觉得诡异,问道:“任绘还说过什么?”
“任队也不敢确定这几具尸体和盲刀案有没有关系,但是他们身上都有同一个人留下来的指纹,也就是水库里死掉的那个人。”
‘他’死了?
汤麦再次翻开现场报告,找到尸体照片,反复确认,仍然不敢相信。
“最奇怪的是,这具出现在水库的尸体是被凶手恶意毁容,浑身上下只留下一处可以用来辨认身份的部位,也就是他的右手。而且,而且……”
一颗磨损严重的弹壳被放在汤麦的手心中。
“是我在现场捡到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任队报告,觉得还是先交给您处理比较好。”
编号0011239,是宇唐的警号。
汤麦的大脑嗡的一声炸开。
他在哪里,又经历了什么,现场为什么会有他配枪的子弹,以及这具尸体和盲刀案到底是什么关系……一连串的问题如同沸腾的水,被罩在雾气中的人看不见来路也找不到方向,当汤麦再次看向那些未知来件时,突然像是抽干了灵魂般手脚冰凉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