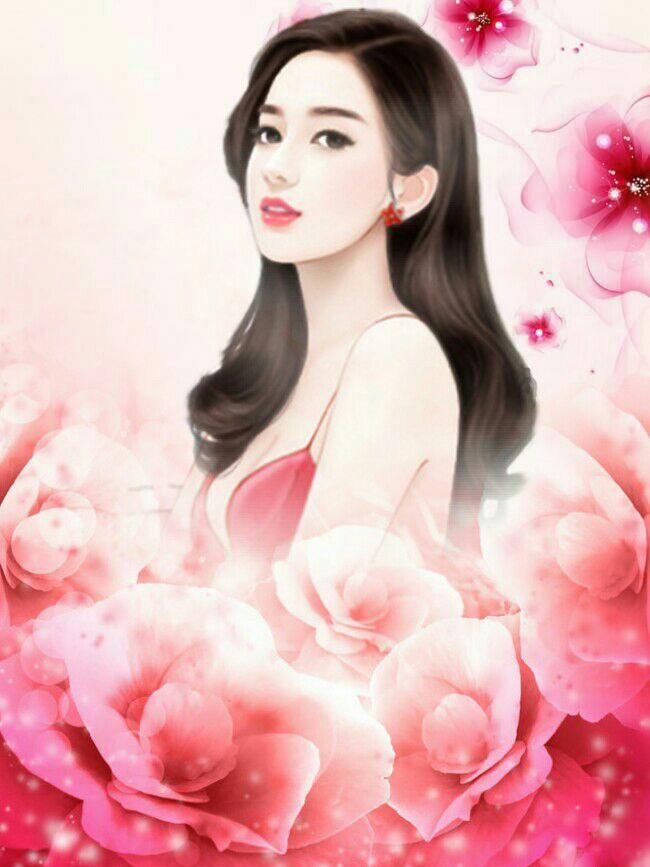全本小说>倾歌令苏倾温容 > 第100章(第1页)
第100章(第1页)
顾奕清被这话惊了一惊,心想这丫头也太过霸道,问:“就是因为这个,你才十九岁都未出嫁?”
“才不是!”苏倾为自己辩解,“在我们那里男子满二十二,女子满二十才可以出嫁,再说,我还在上学,怎么能嫁人呢?还有,我们那里,要是男子娶两个老婆可是会犯法的!”
“你们那里……”顾奕清纠结地皱起眉头,“那娶到不合心意的女子,岂不是要悔恨一生?”
“可以离婚呀,”苏倾摊手,“一拍两散,大家再重新找嘛。再说,我们那边也不像这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每一对儿夫妻都是像我跟温容一样,先相处,互相喜欢,再结婚。是不是比你们这里好多了?”
顾奕清根本想象不到她口中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只是叹了口气,欲言又止。
苏倾见他这样子,眼睛暗了暗,随即又抬起头:“我知道你肯定不相信温容肯只要我一个,可是先王不是也一生钟情于你姑姑?不管怎么说,我都相信他不会背叛我。”她从来就知道温容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顾奕清见她这样坚定的样子,也只好笑了笑,道:“但愿吧,”他顿了顿,“只是先王再钟情姑姑,也还是有个白氏王后?你……你若是当了王妃,也是一样的。”
是啊,即便她当了丞相的义女,身份也绝不能当得上王后,到时候他会怎么办呢?苏倾有些泄气地垂下头。顾奕清见状,赶忙出言安慰:“算了,这都是将来之事,放到以后再想不迟,船到桥头自然直,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嗯,我知道了。”苏倾勉强笑了笑,安慰自己,一切都会有解决的办法,无论他是什么身份,都还是她的温容。
她想着他从前的信誓旦旦,强自按下了心头的不安。
入顾府,重聘红妆(2)
苏倾想象的不同,顾丞相并不是个性格鲜明的权臣,倒像是个中规中矩的文人。又或许有大智慧的人,都会将自己的才智藏在内里。这个人,不动声色地运用权谋,朝堂之上这边心机一点那边一点手段,逐渐一手遮天,无人能敌。
在见她之前顾奕清向他说过温容的意思,他必须要遵从的同时,心里还是有些不满,觉得温容为了一个女子这般有些不成体统。所以在见苏倾的时候拿腔拿调的,心里有些轻视这个出身卑微的丫头。
苏倾知道这一点,在他跟前一点活泼的样子都没有显露,装成像这时代其它女子一样温婉端庄的模样,恭顺地垂首答话,全不失体统,而且也学着他文绉绉地说话,出口成章,抓住时机好好把自己的才华显摆了一通,把旁边看着的顾奕清都惊得目瞪口呆。
苏倾别的不敢说,对古代文学还是精通的,谈吐间处处引经据典,让顾丞相不由刮目相看,逐渐收了之前把她当成红颜祸水的念头,反而对她生出几分敬佩来。他心想,原是自己错想了均昱,他自小就是个励精图治的,怎会玩物丧志将心思放在美色上?果然这女子相貌不足以惑人,见识又实在不像寻常女子,真能伴他左右,于社稷是百益而无一害。
一上午谈话下来,这个义女收得顺顺当当,也满意至极。他问了几句她从前的事,知道传闻中的药王将青黛赠给她,略一思忖,道:“既你与夷尘有交情,对外便不说是义女,只道是自小体弱多病,托与药王谷养大的,如今大病初愈接了回来罢。”药王谷从来被视作仙家之地,夷尘更是威望极高,这样一来对她也有好处。
苏倾见他为她考虑,欢喜地答谢应了下来。离开他之后。她便去寻了司徒瑾,叫他跟夷尘说这事,让他帮帮忙,不要说漏嘴了。司徒瑾嘴上损了她几句,却还是找了鸽子来喂了药蛊给他传信去。几日之后便有回信,说阿倾这样的好姑娘有事相求,他怎么都要应下,还叫她无需道谢。
司徒瑾只好对着信翻白眼,心想这丫头完全没有一点女子该有的温婉样子,怎么竟能得到这样多人喜欢,瞎了眼的人真真不止温容一个。
这边顾奕清看到她轻轻松松讨得自己向来严苛古板的父亲的欢心,对她更是又好奇又崇拜——她怎么看都不像那种酸腐文人,怎么一到了父亲面前,竟能摇身一变成了个满腹诗书的才女?想他自己,从小只练武习兵书,对诗词歌赋可是一点都看不下去,见到她,本以为碰上了同类,没想到这丫头这么厉害——她的家乡,一定是个神奇之地才对。
苏倾只好对他说,她在顾丞相面前端得快要疯了,她自己根本不喜欢这样的相处。人与人之间交往,何必非要这么讲究?他给她的感觉,怎么都像是师长,却不是亲人。相比之下,她还是跟喜欢顾奕清带给她的感觉,轻轻松松地相处,像是真正的兄妹一样,多好。
顾奕清深以为然,心里与她更亲近几分。
这些时日温容一直在王宫里忙即位的事,没顾得上来顾府,苏倾便一直从顾奕清嘴里得到些关乎时局形势的话。
由于准备充足,权势早已全在他手中,这场变乱可以说是漂亮至极,兵卒都没有费几个,杀了些愚忠的异见者罢了。不过识时务的人自然占多数,据说温容进宫的时候,连温均荣贴身的太监都躬身相迎,那些奴才险些赶在他之前杀了自己主子邀功。
温容登基的时候很低调,没有做出什么大的动静来,只是大赦未郡,并免了三年赋税以示恩德,而并未做出什么劳民伤财的庆典。这一点也让众人称道,时人只说国君之位终于回到正主手中,奸孽得除,贤君终掌江山,竟自发地庆贺起来,扶安城里吹锣打鼓热闹了好几个日夜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