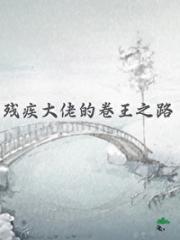全本小说>南华曲全文免费阅读 > 第113章(第1页)
第113章(第1页)
如此一说,南唐君臣自然欢喜。王知朗迅速将和约写好,李璟看了看,取来帝王私印盖了,又递给赵匡胤。赵匡胤通读一遍,觉得无甚大碍,便收在了袖中,又问李璟要了两匹快马。李璟如今视他如鬼怪,恨不得早早送了去,哪里还有留他住宿的心思。
赵匡胤与候在外间的武义律各骑一马,离开栖霞水居时,已过了四更。院墙之内隐约传来哭泣之声,想来此刻江南君臣正在抱头痛哭。赵匡胤冷笑一声,径自驱马往栖霞主峰凤翔峰驰去。武义律虽疲惫不堪,却不敢询问,只得紧紧跟随其后。
凉凉的山风在耳边呼啸而过,急速的马蹄声在静谧山间回荡开来。赵匡胤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随着马背的颠簸而沸腾不止。江南,江南。
到达山顶时,天已微微发白。晨光微熹如雾,浮光蔼蔼,旭日躲在云海后面,像是挣不开夜的缠绵。天空中还有几颗星星,固执地不愿离去,顽强地从云中露出头来,闪烁着微弱的星光,投下不可察觉的光亮。
赵匡胤默默凝视着周围的一草一木,一星一云,许久,又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手像是凝聚了半生的力量,强壮、有力,挥舞间,天地为之色变。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温和而单纯,静静地感受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这便是自己奋力追求半生、终于一点一点收归手中叱咤风云的感觉。”他隐忍了多年的欲望在此刻喷涌而出。天际边上,初升的阳光透出了第一缕金光,这预示着昏暗的夜到了尽头。尽管新的一天仍未苏醒,但这夺目的晨光足以让人鼓起无限的勇气,借着消褪的夜色,接近光明。朝霞渐渐扩散,头顶原本如蓝丝绒一般的天色也被柔和的晨光映得淡了些。天边的缤纷从一个最浓的金黄色亮起,短短一瞬,半边的天色竟成了透明的蔚蓝色,光影离合之间,一轮硕大的新日蓬勃而出,顷刻照亮了世间万物。
“是日出。”武义律为眼前绚烂的景色震惊,忍不住开口。
栖霞寺的晨钟悠然响起,传递了千年的古朴钟声在山谷间回荡。赵匡胤往栖霞寺的方向悠悠望了一眼,绵长的目光又投向的金陵城的方向,想象城中繁华的市井街道,车水马龙的人流,往来不绝的商贾,终于,他的目光还是移开了,转向更远的西北方。
那,是陇西的方向。
转朱阁
文德殿上静悄悄,柴荣把所有的奏折都看完了。
三十五岁的皇帝,浑身正散发着一股不知疲惫的精力。他有些微微兴奋,脸颊都泛着光,他搓了搓手,将手边大杯的黑苦茶一饮而尽,头脑中的思绪便愈发清晰敏锐,他能清清楚楚地记得赵匡胤每一封奏报的内容,何时何地拿下州县多少,收缴兵士多少,围困金陵多日,消耗粮草多少。与江南苦战多年,到今日也算是收获硕硕战果:州十四、县六十、户口贰拾贰万六千五百七十四,人口百余万。比这些数字与财富更重要的是,江南被彻底打趴下了。九月廿一,被剥夺了帝号的李璟命人送来书信,为表示对大周天子的敬意,为避郭威高祖父的名讳,他将自己的名字由“璟”改成了“景”,并以藩臣的名义,给柴荣上表,称“微臣退思,所享以极,岂于殊礼可以久当,伏乞皇帝陛下,深鉴卑衷,终全旧制。凡回语命,乞降诏书,庶无屈于至尊。且稍安于远服,乃心恳祷,无所寄言。”随表附上的除了长长的礼单外,还有将随周朝大军一并到汴京的工匠、艺人、医者、僧侣等共计二百二十三人。名单上,栖霞寺僧人恒超将替国祈福,弘佛法于中原。这个名字,柴荣倒是有些印象,赵匡胤直达御前的密奏中提及过,隐约似乎与先帝嫡子的密事相关。想到此事,原本满心的宏图大志也难免一滞。
自继位以来,收淮甸,下秦凤,平关南,算得上尽心尽力的,可偏偏并非先帝亲生。嫡子之案便是柴荣的心病,柴荣皱了皱眉头,暗自思忖:“这样的人,自然不能留在江南。”朱批刚好写完,小太监便来奏报,侯王到了。
侯王与赵匡胤处处针锋相对,如今赵匡胤大胜归来,侯王在朝中的风头也被抢了不少。柴荣本想在侯王面前得意一番,见了老丈人,却又改了主意。总不能让赵匡胤恃宠而骄了,平衡之道才是帝王权术。
侯王今年刚满五十,圆圆的脸,看上去永远是一团和气,实则是十分精明,站在御座下首,悄悄道:“赵玄郎不日将要回京,陛下看此番该如何封如何赏?臣也好让下头人拟了上来。”
这个问题柴荣自然早早便想过,今日他倒想听听侯王的意思,“此番出征,玄郎大功于社稷,总归不能委屈了,以免寒了将士的心。”
侯王不住地点头称是,倒让柴荣有些意外。“的确不能寒了将士的心,只是兵部认为玄郎应当趁胜追击,夺下金陵。他阵前犹豫,倒有贻误战机之嫌。”
这个论调,柴荣早便听过了,不过是一帮书生之见,便抬了抬眉头,道:“你怎么看?”
“兵部的人没几个上过战场的,都是纸上谈兵之流,哪里真正懂得什么叫贻误战机。灭国之战耗得是长线,条件毕竟还不成熟。眼下能将淮南收入囊中,解决了江淮地区的威胁,另一方面,软弱乖顺的南唐是控制江东地区的最好人选,毕竟要管理这么大一片疆土,时间和人力上开销都不是小数。”
侯王所言正是柴荣心里想的,他点点头,赞许道:“能看清时局,不逞勇贪功,正是玄郎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