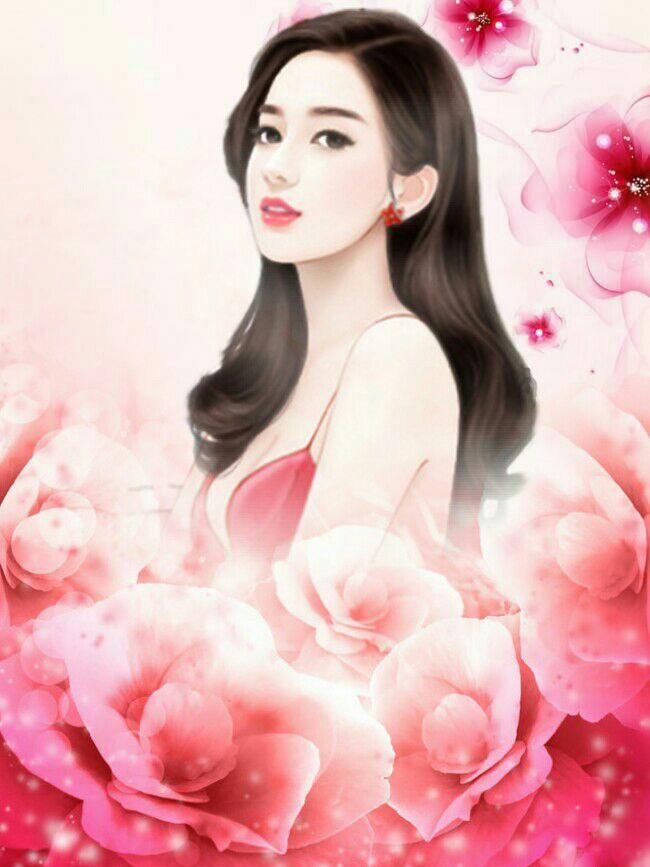全本小说>烽火番外 > 第20章(第1页)
第20章(第1页)
“你现在有主意得很,我管不了你了!”陈彦达怒冲冲地摔下饭碗,扭头上了楼。
第十七章舍不得
姜培生的指挥部在新民门附近的一处民房里,晚上八点半,他把一盒哈德门香烟扔给了手下的连长,问:“你觉得下午那女的怎么样?”“哪个女的?”连长抽出根烟点上。“来找我的那个。”姜培生说。“营长,她是你女朋友?”连长想了下说:“叫婉萍是吧,我记得你之前提起过。”姜培生点了下头:“嗯,问你呢,说话。”“挺标致的,瞅着就知道是大家闺秀,”连长笑着说:“难怪要折腾你这么久。”“主要是她爹事太多,拖到我快三十了还不给个准信,”姜培生闷声说:“我再不成家,就该出家了。”“妈的,糟老头子!”连长弹了弹烟灰:“不成您换一个呗!反正女人都那样,脸蛋身材好,弄起来得劲就行了,不然指着她给你上课吗?营长,您什么时候想开了要找个乐子,我带你去啊!我知道几个活儿顶好的。”“快拉倒!你那些都是什么货色,”姜培生嫌弃地撇嘴角:“我跟你说,你最好少去,小心染上脏病!有钱不如攒着,过两年在老家好好讨一房婆娘。”“咱营长金蝉子投胎的,”连长笑嘻嘻地说:“我是猪八戒,没那口荤腥活不下去。说起来,营长,你能借我*两块钱不?”(*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初期法币与银元的兑换为1块银元兑换1元法币。)“干嘛?”姜培生蹙起眉。连长回答:“这阵子紧得很,等风头过了,我不得去快活下。想找个好的,但咱兜里不是……”“皮痒了吧?你上次借我的都没还,这就又敢来。”姜培生抬手照着连长的后背打了一巴掌。他手劲儿忒大,打得连长一个踉跄从椅子上掉下去。就在脑袋戳进火盆里前,姜培生一把把连长捞住,啧啧嘴,说:“借你也行,帮我个忙吧。”“干什么?”连长抬头问。姜培生叹了口气:“我最近痛定思痛,觉得我跟陈婉萍的事情主要还是我这人太讲究。要是早点把该办的事情办了,在肚子里揣个小的,她爸哪来那么多屁事儿挑剔我。”“那倒是,”连长说完,问:“您的意思是……”姜培生指了下窗外:“我等会儿开车出去一趟办点事儿。”“开车?”连长想了下,一惊:“那辆庞克亚…
姜培生的指挥部在新民门附近的一处民房里,晚上八点半,他把一盒哈德门香烟扔给了手下的连长,问:“你觉得下午那女的怎么样?”
“哪个女的?”连长抽出根烟点上。
“来找我的那个。”姜培生说。
“营长,她是你女朋友?”连长想了下说:“叫婉萍是吧,我记得你之前提起过。”
姜培生点了下头:“嗯,问你呢,说话。”
“挺标致的,瞅着就知道是大家闺秀,”连长笑着说:“难怪要折腾你这么久。”
“主要是她爹事太多,拖到我快三十了还不给个准信,”姜培生闷声说:“我再不成家,就该出家了。”
“妈的,糟老头子!”连长弹了弹烟灰:“不成您换一个呗!反正女人都那样,脸蛋身材好,弄起来得劲就行了,不然指着她给你上课吗?营长,您什么时候想开了要找个乐子,我带你去啊!我知道几个活儿顶好的。”
“快拉倒!你那些都是什么货色,”姜培生嫌弃地撇嘴角:“我跟你说,你最好少去,小心染上脏病!有钱不如攒着,过两年在老家好好讨一房婆娘。”
“咱营长金蝉子投胎的,”连长笑嘻嘻地说:“我是猪八戒,没那口荤腥活不下去。说起来,营长,你能借我*两块钱不?”(*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初期法币与银元的兑换为1块银元兑换1元法币。)
“干嘛?”姜培生蹙起眉。
连长回答:“这阵子紧得很,等风头过了,我不得去快活下。想找个好的,但咱兜里不是……”
“皮痒了吧?你上次借我的都没还,这就又敢来。”姜培生抬手照着连长的后背打了一巴掌。他手劲儿忒大,打得连长一个踉跄从椅子上掉下去。
就在脑袋戳进火盆里前,姜培生一把把连长捞住,啧啧嘴,说:“借你也行,帮我个忙吧。”
“干什么?”连长抬头问。
姜培生叹了口气:“我最近痛定思痛,觉得我跟陈婉萍的事情主要还是我这人太讲究。要是早点把该办的事情办了,在肚子里揣个小的,她爸哪来那么多屁事儿挑剔我。”
“那倒是,”连长说完,问:“您的意思是……”
姜培生指了下窗外:“我等会儿开车出去一趟办点事儿。”
“开车?”连长想了下,一惊:“那辆庞克亚?营长,那车不好动吧,上头要的东西。”
“我开一下能怎么样?那种高档车,你不想摸一摸?”姜培生说着拍拍衣服站起来,长叹口气:“主要是读书多的不好骗啊,非得有点她平时摸不着的东西才能在晚上约出来。”
连长摇摇头:“营长,现在风头太紧了,为个女人太不值当。”
“你不懂,越危险才越刺激越感人!咱这就叫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姜培生说着笑起来,从兜里翻出来两块钱递给连长,说:“我在城外办事儿,出去一个小时。万一不走运巡查队来了,你给我打个马虎眼。”
“成吧,”连长犹豫了下把钱揣进口袋,啧啧嘴:“营长,我泡妞花钱,您泡妞费命啊。”
婉萍在衣柜里挑挑拣拣半天,最后选了一条藕粉色的羊毛呢旗袍裙,立领,领口上绣着两颗艳红色的小樱桃。这是淑兰送给的,说做短了穿上不好看,闲置着也是浪费,不如送人。
“如果你也瞧不上,那就只能扔掉了。”她说话时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婉萍心里明白,裙子就是淑兰专门送给她的,因为前些日子俩人出去喝茶时她瞧见了自己常穿的那条裙子袖口已经被磨破。淑兰从来是嘴巴坏心肠软的,她关心你也不会说关心的话,总要拐弯抹角的给找个潦草理由,像是做的一切行为都只是捎带手而已。婉萍收下了裙子,但也没有白拿,她家里没有淑兰那样宽裕,回礼送不起贵重的,就在晚上帮人家翻译十来份文件做答谢。
晚上八点,婉萍穿好了一身,里面是藕粉色的旗袍裙,外面是灰色的呢子大衣。她坐在窗前,认真涂上口红,正红色的这支是去年姜培生送她的生日礼物。之前都只涂薄薄一层提提气色,但今日婉萍涂得很厚,粉白的脸上艳丽的红唇在夜色下总像是酝酿着一些别样的情绪。
八点四十五分,婉萍已经等在院子门口,只要响三下敲门声她就能立刻离开。夏青注意到了婉萍整个晚上的异常,从屋里走出来问她:“婉萍,你心里到底装着什么事儿啊?这么打扮真的是为了给学生补课吗?”
婉萍摇摇头,她没心情再多解释,只把夏青推回房里,说:“我这么大了还不能有点自己的事情吗?姨母,你就不要管我了。”
夏青见婉萍这样也只能叮嘱她:“现在外面不太平,你一定得小心啊!别再做些让你父亲担心的事情了。”
“晓得了晓得了。”婉萍烦躁不安地说完又走到院子门前,她搓着手,每一分钟都无比煎熬。
“咚咚咚。”第三声刚落下,婉萍立刻打开门走了出去。巷子里一点亮光也没有,黑黢黢的,只能隐约看见一个身影。姜培生伸手拉住了婉萍的胳膊,两人慢吞吞地往巷头走,谁都没有说话,只静静地听着周遭细微的动静。
走到巷子口时,姜培生拉开了副驾驶的门让婉萍先上去,自己特意从后面绕过,走到后备箱时貌似无意的将手搭上去,然后狠狠按下,听到一声轻微的“咔哒”后快步走到驾驶位。
姜培生坐上车后长出了口气,然后踩下油门,车子猛然一动,差点撞在前面的墙上,后面接着传来“嘣”的一声闷响。
“你小心些,”婉萍拉住了姜培生的胳膊。
姜培生啧啧嘴,侧过头向后面问:“后备箱里有几个人?”
“两个。”陈瑛的声音从后排座下传来。
姜培生缓慢踩下油门,他一边倒车一边说:“这种高档洋车我不太会开,路上要是有颠簸或者急刹,你们忍一忍千万不要发出声音。”
“你怎么弄来的这种车?”陈瑛问。
“今天上午缴获的赃车,一家人想往外面跑,被我扣了。”姜培生回答:“你们也是运气好,遇上了一辆后备箱改装过的。要是普通的庞蒂克一个人塞进去都费劲儿得很。”
“你为什么要扣他们?”婉萍问。
“他们主要抓你表姐那种红的,但顺手也会逮几个通日的吃油水。今天上午,有个胖子带着老婆、儿子和一后备箱的美钞金条要从新民门出去。红色都是穷光蛋,就他掏钱贿赂我的手笔保准跟日本人脱不了关系。我这人讨厌小鬼子,但更讨厌二鬼子,撞我这里算他们不走运。”姜培生说:“那人一家和钱被宪兵队的带走,车子被上头的某位瞧上了,不好在宪兵队处理就先放我那,明天会有私人来开走。你们也是够运气,正好能蹭上这波,要不是有他们,今天我也没有半点办法。”
从丁家桥到新民门只有三四里,姜培生说着话,一脚油门的距离就到了新民门门口,守城的士兵见到是姜培生开车后向他敬了个礼,然后递过来一个本子让他签字。
姜培生从大衣兜里拿了包烟放在了本子上,然后推给守门的士兵说:“我出去巡查一下,半个小时就回来,你和弟兄们抽两根烟,休息休息。”
“营长……”守门的士兵很是犹豫,手里拿着本子,既不敢强迫姜培生签,也不敢就随便拿回来。
姜培生往陈婉萍身上瞄了一眼,指关节敲敲本子,沉下脸,显出不耐烦:“怎么这么没眼色?我带个大活人还能跑了?你们连长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