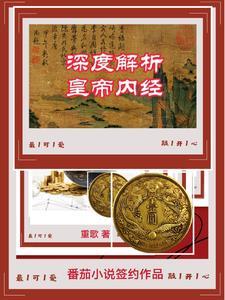全本小说>辨材须待七年期哲理 > 第61章(第1页)
第61章(第1页)
戴文嵩:「不是士兵……是私兵。一切都……於理不合。皇子私囤兵马,是大罪,逼宫更是……」
戴珺语气中已然有几分讥诮:「於理不合,用上的时候倒没有这般顾虑。」
「珺儿,你不明白……那时候我也不明白。」
正当性,对一个帝王来说有多麽重要。
在聂弘盛未得到至尊之位时,「得到」是最重要的事。走上至尊之位後,「天命所归」变成了最重要的事。但显然他不是真的受命於天,他是逼宫得来的皇位,这个事实使得聂弘盛如坐针毡,是他稳固宝座上的一道裂痕。
先皇已逝,原先不站在他这边的知情人都已灭口,而唯有……那麽多的,曾经站在他身後迫使先皇传位於他的人,成了他的心腹大患。好在他们本就是他的私兵,跟随他的那几年也没见光,於是聂弘盛自导自演了一出「废太子之乱」。
第40章别看内容花哨又艳情,道理没错嘛
戴珺说了下去:「他曾经承诺给追随他的这些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其中只有最少数边缘的那些人被留了下来,逼宫这种绝密事,他们当年还不够格知情。今上也依然相信他们,相信全天下对他最忠诚的就是这些人。而真正跟着他出生入死的人,被他用一纸密令带到寅河谷。这些人得到的命令是在寅河谷下,假扮废太子的残部,引诱废太子的人同他们一起穿越寅河谷,後等追兵到了,好前後夹击他们,将叛军困死在山谷中。如果我没猜错,事发仓促,他们对皇帝的密令也不疑有他。而新登基的这位皇帝,早传令给在苏埠的守军将领,命他们夜间埋伏山崖,而後推下落石,倒下火油。他给苏埠守军的说法是……剿灭废太子的残部。」
戴文嵩没有否认,眼中有了几分颓然和羞愧意味:「江大人他,已经全都想起来了麽?」
戴珺微微摇头:「只言片语,儿子做了些拼凑和揣测。」
「我当年……也是自己猜出来的,」戴文嵩听起来很累了,言辞从喉咙里滚出,好像从结痂的伤口上蹭下一块什麽东西。他实际语气平静得惊人,叫人听来却遍体生寒:「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叛军』,是他……容不下这些人了。」
「为什麽呢?当初行逼宫之事,谁也没有万全的把握,他们愿意跟着他冒如此风险。事後即便他们跟着皇帝做下的一切已经不可说,就没有更好的处理麽?依然当做私兵养着就是,为何要赶尽杀绝?」
戴文嵩看着他,那双已然苍老的眼睛看起来却是很亮的:「不……跟着还是皇子的他去逼宫的人,是不会想一辈子做私兵的。」
戴珺恍然明白了。
那也是聂弘盛登基之後才明白的事。从前他没把自己放在皇帝的位置上,他只是一个需要推翻这种建筑的「反叛者」,等他自己登上至尊之位,却忽然发现这不是一场关於谁推翻谁的游戏,而是一盘充满了微妙博弈的棋局。
他成为皇帝,却好像只是成为一座森林的新主人,并没有能耐将这里所有的根系连根拔起,再换上新的植株,他做不到。
当然,也没有必要。
他不是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新开辟了一方国土,有大把空位等待着他放进去自己的人。他只是斗倒了他的兄弟,然後从他父亲手中夺过皇位,他不需要把这里的一切都改天换地,只要原有的人能对他效忠。
他可以用不光明的手段将自己的父亲取而代之,甚至未察觉有多大的阻力,因为对於满朝文武来说,换一个姓聂的皇帝,没有伤筋动骨。如果这些世家大族的利益被牵动,那才是聂弘盛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聂弘盛坐在龙椅上俯瞰百官的时候,他发现了,最差的选项才是把这些人全都换掉,最省力也最稳妥的方式,是稍稍示好就能拉拢已有实权之人站在自己这边。
如果要说得冠冕堂皇一些,这对於天下的稳定来说……也最为有利。
在他还是不受宠皇子的时候,他得不到这些助力,只有那些毫无背景的丶青涩又热血的年轻人会被他口中那个新的天下蛊惑,他也不得不以蛮力丶以鲜血为自己挣出一条前途;
而时移事易,他已是新皇,那些曾经高不可攀的世家大族和实权者,也已是他的臣属。聂弘盛发现他可以有更优雅的方式来确立他的统治,他最有利的武器已是握在手中的皇权,不必用从前做事的方式去获得自己想要的。
而那些本见不得光的私兵里面,却有人殷切等待着新皇登基之後的鸡犬升天,这使他感觉自己的软肋隐隐作痛。
「先皇本让今上留废太子一命,经此一役废太子也顺理成章除去,解决了他的心头大患。这些有从龙之功的私兵,因为本就见不得人,就这样在寅河谷,被他尽数坑杀。」戴珺说,「他还完成了第三件事,因为这场众人讳莫如深的废太子之乱,苏埠守军将领平乱有功,被成功提拔来到陵阳。皇上便顺水推舟,把先皇原本重用的陵阳守军将领换了下去。」
「是……苏埠那位……从前就很欣赏皇上。」又得他提拔,自然是会忠心耿耿。
而苏埠的守军将领也只觉得自己真的是平了废太子之乱,不会怀疑自己坑杀的还有他人。就算有疑惑,但他借平乱之事立此大功,在新朝站稳脚跟,他有什麽开口的必要呢?
一箭三雕,没有旁人全盘知道那个晚上发生了什麽。<="<hr>
哦豁,小夥伴们如果觉得不错,记得收藏网址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