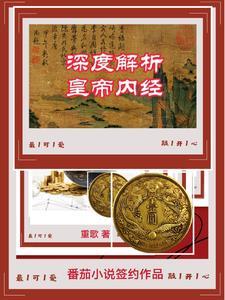全本小说>清远人家私房菜馆地址 > 第24章(第1页)
第24章(第1页)
“许个愿吧。”蒋之屿听见乔述珩在身旁道。
十九岁了。蒋之屿第一次收到这样郑重的生日祝福。他从前的人生颠簸,在此之前,他对于生日的认知就是身份证上一串不起眼的数字,再奢侈点,或许便是街店里有趣的礼品包装盒。
而现在,蒋之屿生日的第一秒,乔述珩端着蛋糕,就这么静静不说话,就这般盯着自己。
简陋的环境,蛋糕估摸早就失去了最好的味道,只剩下蜡烛燃起的光亮停留在乔述珩眼睛里,让一切都随之闪动莹莹。
蒋之屿觉得眼睛酸酸的,但又控制不住自己脸上的肌肉,矛盾得很想笑起来。
乔述珩在蒋之屿泛红的眼眸中望见自己。
他无端想起自己的手臂被宣判死刑过后的一天,他不放弃,还想尝试,结果引发伤口的后遗症再度发作。
乔述珩强忍住肌肉深处的疼痛不出声,在一片冷汗中试图调整呼吸。一直陪伴着他复健的蒋之屿也是红着眼圈,手指缩在卫衣衣袖,只小心翼翼地探出些指尖头攥住自己,企图传递些力量。
最终,疼痛终于缓过去。
乔述珩盯着治疗室的桌面,上边是他复健时颤颤巍巍画出的半幅速写,很简单的静物,不过是一盆多肉,往常三下五除二的功夫即可画出雏形,可这会儿连频繁动用手腕的基本动作都维持不了。
乔述珩望着被自己疼痛时攥在手中、早已变得扭曲的铅笔,复健的不知道第多少小时,他第一次感受到绝望。
乔述珩低着头,思绪顺着折弯的铅笔延展,起初只是注意到掉落在地面的部分铝芯,后来又进一步观测到点点芯灰砸在地上形成的小黑斑。
像是一只只麻雀的眼睛,黑黢黢的,吵闹得瘆人。
乔述珩松开手,用上臂罩住脸庞,遮盖双眼。
彻底没有机会了,乔述珩后知后觉诊断书上“神经受损”四个字真正意味着什么。
治疗室的环境很静,白色的帘子被风卷起,吹到乔述珩手臂的间隙,阳光折在身边,乔述珩却感知不到一点温度。他的眼前只有若有似无的黑斑,模糊重叠在洁白的帘子上,乔述珩闭眼又睁开,可那黑斑却越来越大,像是太阳在白布上烧出的块块黑洞。
乔述珩真的好冷,他下意识裹住自己,却被一个温暖的怀抱拥住。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一直沉默得跟个透明人一般的蒋之屿终于开口,他看着乔述珩的眼睛,一点点挑开遮盖在其目光上边的碎发。
“我在。”蒋之屿半蹲下身,支撑住比自己高了将近一个头的乔述珩,“我会成为你手中的笔。”
蒋之屿想,他要代替乔述珩的手,去替他学习更多的东西,看到更广的世界。
“把你的梦想托付给我,好吗?”蒋之屿抚上乔述珩发冷的手,又紧紧地握住。
乔述珩的眼眸终于清晰。
“可以把你的人生借给我吗。”像是不能饮酒的人偷喝陈酿,又像是干渴至极的人见到海洋,乔述珩顺着蒋之屿的眼睛,开口回应道。
当年是我骗了你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轰隆而行的火车总算要靠站。乔述珩嘴上说着不适应卧铺窄小的床铺,却是能够一睡不起到靠站,就连蒋之屿洗漱的声音也扰乱不了他良好的睡眠,总归还是睡得昏沉,没有苏醒的迹象。
蒋之屿确认了乔述珩还在呼吸,松下口气来。他一并收拾了两人的行李,闲来无事又转到卫生间挤好牙膏,随后默默坐下。
乔述珩总算在火车下站前被手机铃声震醒。蒋之屿连忙将装满的水杯递进卫生间,乔述珩接过,不说话,却也算接受。
蒋之屿在心里松了口气,想上前和乔述珩说话,张开嘴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只好干巴巴顺着翟淇的叮嘱,提醒乔述珩待会下车时记得戴好口罩。
“嗯。”乔述珩偏头瞥了眼蒋之屿,吐着口中的沫含糊回应。
嫩白的牙膏沫落到洗漱台,混着冰凉的水顺溜滑入水管,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再看不到踪迹。
————
蒋之屿和乔述珩准点下车,还没走到和司机约定好的外广场,便见着了专门接送的工作人员。
说是工作人员,但,也是这次回乡的地勤。
蒋之屿望着眼前的男人,不是之前预料的憨厚面孔,也没有中年发福后留下的啤酒肚。
宋中沛是一个很干净的男人,只稍高蒋之屿一点,穿着薄款风衣,一双水汪的桃花眼向上挑,是那种放在人群一眼便能看到的类型。
蒋之屿只稍微与其对视片刻,竟然也下意识脸红。
乔述珩注意到蒋之屿低垂的眼帘,轻哼出声,故意往旁边挪,挤碰到他。
“乔先生是吧,我是这段时间您们回星城的陪同人员,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联系。”宋中沛得体的露出八颗皎洁牙齿,惹得乔述珩眉头微蹙。
他听夏樊怡说过这位安排的陪同人员,也是顶级艺校毕业,工作是策展,算是半个圈子里的人。
愿意撇下工作来做陪同,乔述珩大抵也猜出其心思。
这样的人见多了,乔述珩不想搭理。只收了收下颌,忽略一脸老道的宋中沛伸出的手。
宋中沛却还是一副淡定的样子,礼貌地拉开车把手,小心护住车顶易碰的上方。乔述珩先一步坐到车里,瞧见宋中沛又殷勤地回身,接过蒋之屿手上的行李。
倒是个会来事的。乔述珩心想。
————
星城的机场在县里,距离市区还有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