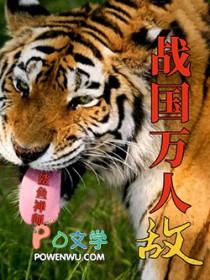全本小说>清远人家私房菜馆地址 > 第20章(第1页)
第20章(第1页)
“自己看看吧。”翟淇扯开办公室的椅子坐下。
蒋之屿踩住其中一张纸的边角,偷偷用脚往自己身边挪动,20的视力足以让他看见白纸上不算小的字体内容。
上边是聊天记录的截图,大抵是关于八卦交易的。
“我还说你打架的消息怎么传得那么快,原来早就中了别人的圈套。”翟淇直着地面上的一张纸,“是有人想刻意挖你的黑料,一开始就守在了录制现场等你犯错。”
“结果没想到遇到了这么劲爆的消息。”
“那个主动和你打架的人,或许就是线人。”乔述珩没有同翟淇说过当天的细节,只从蒋之屿的只言片语凑出了答案。
翟淇的余光绕到身后不时探头的蒋之屿身上,最终也止了指摘。
“总之,这段时间还是按照我和你交代的那样,凡事打报告,不要再被人抓住漏洞了。”翟淇解了乔述珩的绑,蹲下身子,给了他个脑瓜崩。
坐在回程的出租车后座上,蒋之屿打量着身旁的乔述珩,隧道的光不算亮,旁边经过的车灯偶尔透过车窗打在乔述珩的脸上,留下崎岖而逶迤的光斑。
蒋之屿低头,两个人中间隔了段距离,可影子是紧靠着的,长而灰暗的影子挨在一块,彼此相依、融合,最终化为一个整体。
蒋之屿下齿抵住上颚,想说话,却又无从开口。
翟淇在发完一顿脾气后还是同意了乔述珩的出行。她说一切由她安排,又叮嘱乔述珩低调行事。
交代完一切,翟淇又将蒋之屿叫了出去。
“我工作忙,没法跟他走,他这人犟,也就还能听听你的劝告。”翟淇抚平蒋之屿翘起的衣襟,交代道。
蒋之屿面露讶异,尽管翟淇是翟瑛的女儿,但和蒋之屿的关系一般,蒋之屿不是个话多的,两人又有性别和年龄差,大多数时候不会单独相处。
相较之下,乔述珩与翟淇的相处方式倒是像极了一家。兴许是乔述珩从小在翟瑛底下学习,他和翟淇没啥芥蒂,相处起来倒像是寻常人家的懂事姐姐与犯浑弟弟。
蒋之屿记得乔述珩为主角的画作在网上传播后,没过多久当时还是艺人助理的翟淇便主动找了上来,她向公司承诺签下乔述珩一定能有所值,为此还制作了一份近百页的ppt证明选择乔述珩的可行性。不仅如此,她还特别跑到乔述珩的家中,亲自和相对保守且不常回家的乔述珩父母沟通,最终保证乔述珩走上了演员之路。
由此,翟淇成为了乔述珩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经纪人,帮乔述珩从籍籍无名走到小有名气。
乔述珩慢慢从之前受伤的阴霾走出,蒋之屿又考上了美院,一切都在向上向前。
可人生总是段心电图,波折似乎才是主题曲。那之后没多久翟瑛便病了,诊断出恶性胰腺癌,不到三个月便离世,自此,单亲家庭长大的翟淇彻底孑孑独行,牢记母亲的遗言,像亲姐一般拉扯关怀着毫无亲缘的蒋之屿与乔述珩。
现在想来,蒋之屿无疑是感谢翟淇的,是代替乔述珩,也是代替自己。可他也无法纯粹地感激,毕竟,要不是翟淇当年的先斩后奏,或许他还有时间解释,他和乔述珩两人的关系也不至于变僵至此。
何况这些年来,蒋之屿一人出国留学,翟淇对他的关怀也仅限于逢年过节的几句问候,两人总归是生疏。相较之下,同样是翟瑛的徒弟,翟淇对乔述珩的看重简直快从眼神动作里溢出。
蒋之屿的指甲无意识勾住自己的长裤,出租车后座很闷,他的心脏也被压住,不太透得出气。
蒋之屿扩张胸腔,企图吸纳更多空气以舒身。
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就无由来的吸不上气,是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着?他的呼吸紊乱,嘴干得更像是吃了墙灰,涩得发呛。蒋之屿手掌化拳锤着胸口,心烦自己身子的异样。
不过是为了工作回国罢了。翟淇念着故人的身份已经体谅了很多,他现在该做的就是好好把工作完成,至于其他的,多想也没有意义。
蒋之屿头靠在出租车车窗,车速很快,窗外的景色瞬息万变,昏暗得让人看不清楚样态。
蒋之屿朝窗,也不摇下窗子透气,就着时隐时现的汽油味呼吸。气味越来越浓,像是为了阻止蒋之屿睡虫的上头,起初只一段一段,后来便全然萦绕在蒋之屿鼻腔,只稍一吸,重金属的味道便沿着嗅觉神经元传到大脑,蒋之屿被出租车晃得昏昏沉沉,索性懒得再想。
四月中,一切的工作都已交接完毕。
乔述珩穿着自己从意大利定制的高级西服,左手拖着一个26寸的行李箱,右手则拽着一个肩带磨损的背包。
他戴着墨镜站在火车站台上,身姿高挑,尽管旁边尽是拥挤的人群,仍走出t台走秀的气质来。
蒋之屿正拥在几步之遥的前头占位,他的手上提着优惠买来的大支矿泉水,用身躯一点点挤进人潮,为乔述珩开路。
乔述珩几乎是抿着唇进到软卧包厢的。在翟淇同意两人出行后他便打算定机票,结果蒋之屿这厮非不肯和自己一同乘机,而偏要坐上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说是这样才算是完整的回顾。
乔述珩再三强调自己包机票,蒋之屿不同意,留下一句“这是我的事”后直接锁上房门,不再争执。
于是乔述珩只好退了票,包了四个人的软卧包厢。
乔述珩放下行李,坐在蒋之屿已经整理好的下铺。蒋之屿就弯腰在他对头换另一张床上的一次性用品,先是被单枕套,后又拿出纸巾抹桌台,还得喷上点酒精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