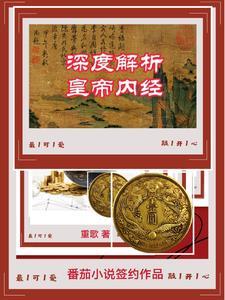全本小说>是将军啊 > 第6章(第1页)
第6章(第1页)
说着,他大步上前,扯下江澜脸上的面罩,脸上并无丝毫讶异,平静道:“我就知道是你。”
江澜顿时愣住,脸上闪过一丝讶异,呐呐问道:“将军……怎会……知晓是我?”
贺长安负手而立,缓缓说道:“前两天追查刺客,我一眼就认出那日从房梁上掉落之人是你。”
江澜心中一慌,连忙解释:“将军,刺客不是我!那次与将军在玉妙苑分别后,我便对将军钦慕不已,所以那日才会趁月色前来探望,绝无恶意!”
贺长安目光如炬,盯着她道:“我自然知晓刺客不是你,当日夜里有两个刺客,一真一假,你便是那假刺客。”
江澜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当时从自己身旁拉走的女子竟是真刺客!
江澜察觉自己做错了事情,但是又不敢跟面前的人讲,只能弥补于贺长安。
她眼珠一转,又道:“大人英明,明辨是非,小女子愿追随大人,效犬马之劳,不知大人可否应允?”
贺长安盯着她,沉默许久,忽然道:“我若不愿呢?”
江澜轻轻勾唇一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大人若是不愿,小女子钦慕将军已久,无奈之下,怕只能以身相许,哪怕做个妾室也好。”
言罢,她伸出手,假意欲解开身上的夜行衣。
贺长安看到这一幕,顿时神色一紧,略显仓促地背过身去,声音低沉,带着几分恼怒:“你若再敢乱动,我便杀了你。”
江澜听闻贺长安拒绝,索性假惺惺地抽泣起来:“既如此,那将军便杀了奴家吧。若不能伴于将军身侧,这余生于我而言,唯有痛苦相伴,生不如死。”
贺长安眉梢一挑,冷哼道:“哼,你既一心求死,那我便成全你。”
言罢,他从袖口处取出一颗小巧的红色药丸,递向江澜。
江澜见状,眼中满是疑惑:“大人,这是……”。
“这是毒……”药。话未说完,她猛地伸手,一把夺过药丸,塞进嘴里,还吧唧吧唧嘴切,还真毒药,真会唬人,明明就是滋补的药丸而已!自己又不是没有吃过。
为了不露馅江澜道:“嗯,味道尚可,不知还有否?”
贺长安被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逗得忍俊不禁,朗笑出声:“你这女子,倒有几分胆色。日后便跟着我吧。好了,回去吧。”
说罢,他将手中的铃铛轻轻一抛,江澜赶忙伸手接住。
“多谢大人。”江澜福了福身,临行前又忍不住问道:“大人,我刚刚所服,可是真毒药?”
贺长安负手而立,缓声道:“此乃毒药无疑,你每月来我处领取解药,方可保无虞。”
“遵命,大人。”江澜乖巧应下,莲步轻移,转身没入夜色之中。
身影渐远,直至被黑暗完全吞噬。
言玉这时从夜幕深处缓缓走出,眉头微皱,面带疑虑:“大人,此女来路不明,真要将她收入麾下?”
贺长安面色冷峻,目光深邃:“你且去仔细调查她的背景与身份,是否清白干净。若有一丝细作的嫌疑,不必留情,直接诛杀。”
言语间,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开来。
“是,属下遵命。”言玉抱拳行礼,领命而去。
…………
次日,她便被传唤至贺长安的书房。
“乔雁并非你真名吧?”贺长安目光如炬,直勾勾地盯着江澜,率先发问。
江澜微微福身,不慌不忙地答道:“大人明察,奴家本名江澜,乔雁乃是家姐之名。三年前,我姐妹二人于玉妙苑艰难求生,相依为命至今。
奴家生性喜自由,不愿被拘束于一方天地。那日大人所见,原是家姐身体抱恙,才让奴家代为舞上一曲。”她言辞恳切,态度坦诚。
“你爹娘呢?可还有其他亲人?”贺长安继续追问,声音沉稳而冰冷。
江澜微微垂首,眼中闪过一丝哀伤:“奴家爹娘早亡,自幼便是姐姐含辛茹苦将我拉扯长大。我们孤苦伶仃,在这世间再无其他亲人。”
内心却暗自祷告:爹娘,孩儿不孝,万万莫要怪罪。老天爷,可别降罪于我,此皆为无奈之言呐。
贺长安微微点头,视线落在手中的资料上,上面显示一切,背景干净清白。
江澜心中窃喜:幸好我早有筹谋,事先打点妥当。若被你查出破绽,我岂不是小命休矣。
脸上却依旧保持着恭敬与温顺。
“自今日起,你便负责护卫将军府安全,充任护院之职。若无他事,便可退下了。”贺长安面无表情,声音平淡无波。
江澜闻言,顿时愣在当场,嘴角微微抽搐:“………”。
心中暗自腹诽:闹了半天,竟然只是个看院子的!那我之前又是何苦来哉?这般折腾,到底所为何事?当真要被气死!
江澜满心气恼,转身走出屋内,来到门口,仰头对着天空,有气无力地发出一阵狂吼。
贺长安正安然坐于书桌前,手中毛笔轻蘸墨汁,在信纸上写道:“林兄,近日偶遇一女子,甚是有趣。明日你我可否于茶楼一叙?”
装可怜月下轩的雅阁内,两名男子……
月下轩的雅阁内,两名男子正相对而坐。其中一位面容清俊,透着温文尔雅的气质,另一位则身材魁梧,散发着雄壮威武的气场。
江澜眉头轻皱,带着一丝无奈与为难说道:“贺兄,上次您给小弟的建议,小弟怕是难以施行。您也知晓,小弟家母重病在床,家父又早已离世,家中需有人时刻照料,实难分身。”
贺长安微微颔了颔首,神色平静:“无妨,林台兄肯与贺某一同筹谋商议,对贺某而言已是幸事。只是不知明日林台兄可有闲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