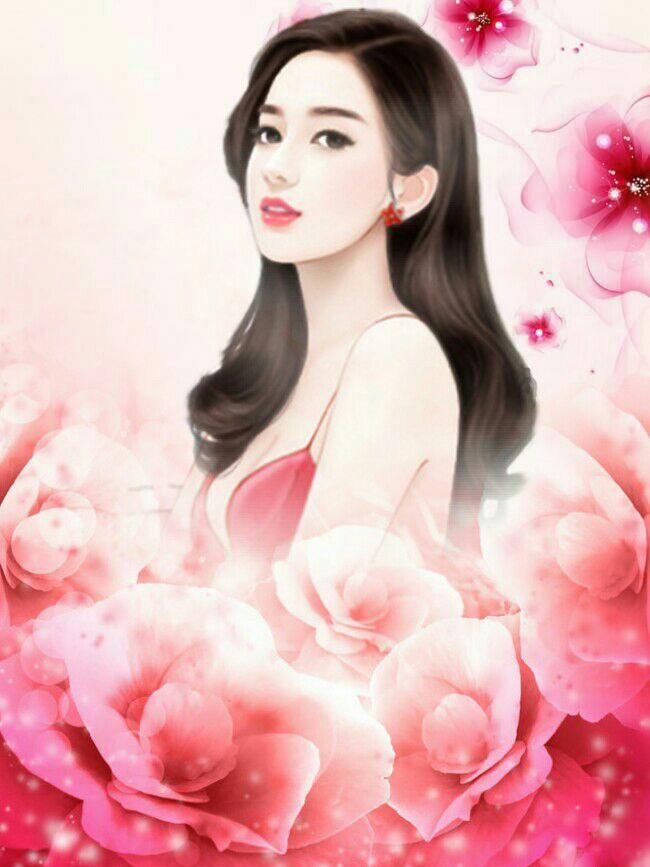全本小说>将门低调生活小记免费阅读 > 第30章(第1页)
第30章(第1页)
“哦?你说。”
“鬼卫们输送消息,必是用极安全的方式。不能是口舌相传,也不能是密信,否则日子一长肯定会露马脚的。”
“没错。毕竟他们的动作比蚂蚁还频繁呢。”周魁期待地望住她。
雪砚微调坐姿,直视他说:“真相简单极了,揭示叫你气炸也说不定。”
“哦?”他真有点抓心挠肺了。
“方才游园时,我不时发现墙上、穿廊里经常有一些镂花小孔。挺奇怪的。”
周魁不解道:“有何奇怪?不过是些建筑装饰。”
“可是,墙上镂空无非是为移步换景。那些孔的位置大多不太起眼,尺寸也不够大。寻常人不带心眼儿,不会关注到它们的存在。”
周魁蹙眉不语。
雪砚凝望他说:“还有,那些孔的形状都不同,有十字花,有菱花,也有圆孔,间距也都不一样。但是它们无一不是横二十竖九的排法,总数都是一百八十个。四哥,这就不正常了。”
周魁的脸阴沉了,目中有了电闪雷鸣。
静了一会儿才道,“你是说,他们利用这些孔眼递消息?”
“是的。这种规整的阵列可形成天然的密约。一个孔代表一个字,几个字或一个情境,具体如何,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密约(密码本)。旁人是不得而知的。”
雪砚慢慢地说,“举例来说,某一日将军遇刺、夫人受惊了。我们院中某人只需跑去后舍穿廊里,往几个孔眼里摆些小树杈,或者小石子儿,消息就长翅膀飞起来了。而无关的人就算见到了,也不会觉得有何不妥。”
周魁被九天神雷轰了一般,一动不动地坐着。
雪砚又轻声道:“她的下家不需碰面,也不需密信和传话,只需来穿廊里瞄一眼,就掌握四哥的动向了。接着,在下一组镂花孔里同样操作。直至传到玄女娘娘庙,由女道士们用木鱼声和钟声把消息给出去。”
“这就是我看到的。”她如是概括道,“四哥,是不是好简单?”
周大将军一时无言。眯眼凝思,拳头慢慢握了起来。
指间炸起了一阵凶残的轻响。
雪砚吓得一悚,猫一般直盯着他看。周魁眨一眨眼,安慰道:“无妨。为夫只是气自己在这儿住了两年,竟从未注意过镂花孔的数目相同,阵列也相同。”
“我想一般人都不会太注意的。”雪砚说,“谁会像我这呆子喜欢数数呢?而且,所有这些地方都不大引人注意。要么在凹角旮旯里,要么旁边有不少景观,吸走你的视线。”
周魁点了点头,不言语了。
深锁浓眉,良久地陷入了缄默
她的发现虽叫人匪夷所思,却能完美地自圆其说。不得不承认,即便在没有进一步验证的情况下,他已有七八分相信了。
毕竟,八处同样排列的镂孔不像是偶然。用来递消息也完全可行——所以在建府之初,皇帝就让人把精密的手脚给他做下了!
想到这两年费尽心机地排查,周魁真是黑血翻涌,一肚子黄风雾气。
书房里一时无声。
静得能听见思想在“咯吱”、“咯吱”地蠕动
雪砚端庄地坐着,由丈夫去仔细推敲她的发现。渐渐的,渐渐的,她的目光虚化了。三魂七魄离了体,变成书虫钻进一旁的书架上去了
过好一会才听见:“雪儿,雪儿”他喊了好几声。
雪砚猛一回神,两眼迷瞪瞪的,“诶?”
周魁等她定一定,才低声问道:“假如多观察一些时日,你能反推出他们的‘密约’内容吗?”
“嗯。镂孔的密约很好反推的。我们只需干一些特别的事,看他们摆了哪些孔,多来几下就能猜到了。木鱼声有点麻烦,但也并非不可能”
“好。”周魁目蕴精光望着她,低沉而又铿然地道了句,“很好!”
“四哥,要是反推出来了,你打算怎样对付他们?”
他微微一笑,当然是要把皇帝也怄出三升血才行!
可他并不这样说,反问道:“依你之见呢?”
“我也不懂权谋之事,不敢妄言的。”
他以肘部拄着腿,带着一丝浅笑凑近她:“臭丫头,在后院你不是有七八条诡计、妙计和毒计么,怎的到了这里倒又装乖了?”
她又红了脸,轻声道:“谁叫你往这儿一坐怪吓人的。既像你,又不太像。”
“哼,胆小鬼。”他又不依不饶地问,“快,说一说你的高见。”
她沉默一会,才说:“我认为,这些人毕竟是皇帝塞进来的。虽然四哥早就有所猜疑,知道是哪些人。但若是我们亲自下手除灭了,倒像有反叛之心。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自己下手,自断爪牙。吃了哑巴亏还怨不得咱!”
周魁一时未予置评。只是目光灼灼的,对她绽开了一个特别骄傲的微笑。
这样的笑,几乎把她整个孤单又无助的十七年都照亮了。雪砚溺在这目光里,心醉得厉害。她痴痴地想,四哥,就这样为我笑一辈子吧!
许久,周魁轻声问道,“你帮四哥拔了心头刺,想要我怎么谢你?”
“我只是基于发现简单地推测一番,还没证实呢。”雪砚说。
他微微一笑,固执地问,“无妨。说吧,想要四哥怎么谢?”
雪砚心动地踟蹰着,抿嘴垂了眼。
她把一句“想看一看你的书”堵在了舌根,感觉比要十万两黄金更难启齿。红脸嗫嚅半天,退而求其次地说,“就是那个,你肚子有八个小块块,让我那啥个够吧。”